什么是“人本主义”?
首先须澄清,“人本”并非‘以人为本’。人本的英文原词humanistic也不能涵盖人本心理学的意思。马斯洛下面一段话倒可以精确地表述“人本”的含义。
数千年来,人本主义者总是试图建立一个自然主义的、心理的价值体系,试图从人自己的本性中派生出价值体系,而不必求助于人自身之外的权威。
与管理界流行的‘以人为本’并不是一回事儿,人本主义的意思仅仅是:人如何就根据自身做选择。
【哲学来源】
人本主义心理学有两个重要的哲学来源:存在主义和现象学。
存在主义的核心概念——being,和核心观点——选择的自由,对了解罗杰斯和马斯洛两个人有很大的帮助。
所谓being,直译即“是”,通常被译为“存在”。存在主义的鼻祖——克尔凯廓尔的一个词语经典地诠释了human being的意思。他说,人要“to be that self which one truly is”(中译:“是其所真是”)。意思即,只有当你果真“to be that self which one truly is”的时候,你才真地达到了专属于你的individual being。克氏把此当做自己毕生的目标。
罗杰斯则从另一个角度说,一个个体之所以出现心理障碍,就因为异化于外在的目标、规则、角色,而把专属于自己的being给丢掉了。
所谓‘选择的自由’,即:一个个人虽然生来就被置于不可选择的境地,但我们仍然有选择成为自己的自由。
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概念充溢着“选择的自由”的意味。所谓“自我实现”,即我选择成为最佳的我,而非被塑造成最有效率的我(行为主义),或我注定不可能成为最佳的我(精神分析)。
概括地看,好似,马斯洛等人一直聚焦在个体的选择的自由上;而罗杰斯则说,你只有拥有专属于你的being的时候,你才有选择的自由。
至于现象学,坦然地讲,无论罗杰斯、马斯洛,还是其它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对布伦塔诺、海德格尔、胡塞尔三人的繁琐的现象学体系,都没有详尽的了解和把握,他们所引入的,只是几个简单的概念和观点。
所有的人本主义者都信奉一个名言:心理的现实即个体的直接现实。
如若放下研究者的眼光,把此名言放在你自己身上,就会明白它确切的含义,即:那些专属于你自己的活生生的体验才是你自己最真切的现实(being)。
“科学”的行为主义,不理会个人的活生生的体验,因为体验稍瞬即逝,不可如物理世界那样可简单重复。无论体验世界何等丰富,他们仍然说,只有S—R(刺激—反应)唯一实在,而体验的东西,只是S—R的积累的幻象。

罗杰斯自己一直也有一个矛盾:作为一个科学的心理学工作者和作为一个主观的治疗者两个身份的冲突。他自己等一段话非常精致地描述了他的矛盾:
我既是一个心理治疗师,从多年来执业于这一令人兴奋的、充满回报的活动中获得了很多体验;我又是一位科学研究工作者,致力于探索心理治疗的真谛。由于这种双重身份,我日益意识到两个角色间的鸿沟。我的心理治疗工作做得愈好——如在治疗过程中那些最精彩的时刻——就愈是忘我,对自己的主体意识浑然不觉;而我的研究工作做得愈好,愈是‘硬头脑’,愈是科学,作为科学家的严格的客观性和作为治疗家的近乎神秘的主观性之间的距离就愈是叫我坐立不安。
克尔凯廓尔的书给了矛盾中的罗杰斯很大的支持。他写道:“阅读他的著作令我放下包袱,使我更信任、也更愿意表达我自己的体验。”
为什么克尔凯廓尔的著作会令罗杰斯放下“包袱”?
阅读克氏的书,会发现,他的体验世界极其精致、丰富,并且,他和他的体验几乎没有什么距离,他直接、坦然地面对自己的任何体验。或许,阅读克氏的著作时,罗杰斯感觉到,一个“to be that self which one truly is”的人的体验世界竟然可以有如此的魅力,从而“更信任、也更愿意表达我自己的体验”。
那么,为什么即便真诚如罗杰斯,也依然有如此强烈的矛盾呢?他的另一段话则揭示了他一点下意识里的东西:
回首过去,我能够清晰地辨认出这个矛盾的起源。这是逻辑实证主义和存在哲学之间的矛盾。于前者,我一直侵淫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熏陶之中,我一直对它怀有深深的敬意;而于后者——主观取向的存在思想——我较晚才有接触,但它很快就在我的心里生了根,因为它于我的治疗体验是那样地贴切。
由此,可以从罗杰斯的个人矛盾引出一个根本性的质疑:为什么心理学非得要执着在从物理学中引入的“科学”标准,而忽视自身的真切存在呢?
联想科学同宗教的近两千年的斗争,缅怀那些为真理而奋不顾身的先驱,你的确不由得会肃然起敬。尤其是,当你肃然起敬的东西已经成为一种标准时,你下意识里如何不对它怀有一种深深的敬意呢?
但问题在于,研究人的主观范畴的心理学和研究物质、宇宙等的客观范畴的物理学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把客观范畴的科学的标准置于主观范畴的学科,可不可能?
从James开始,就已经有人对心理学能不能成为一门“科学”表示怀疑。至今,心理学发展了100多年,对了解、改善人类的生存境地有了巨大的贡献,但整个的心理学却一点都看不出有摆脱库恩的“前范式”境况的可能。
关键的问题也许在于,绝大多数的心理学家一直都把来自于另一个范畴的“科学”标准奉为神明,却忽视了心理学的主观特质。当自己活生生的体验同“神明”相矛盾时,多数的心理学工作者就放弃了自己的直接体验。但真诚如罗杰斯则将这个矛盾保留住,直到他开始接触存在哲学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共鸣和支撑。——说“支撑”,是因为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同‘神明’做斗争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事情。
自然,接触存在哲学后,罗杰斯并未就此摆脱了矛盾,或者说,就把科学检验标准给丢弃了,而是一直都在做科学哲学的探讨,试图寻找属于心理学自己的科学标准。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罗杰斯最终也未找到。他晚年时,有人提出“软科学”的概念,试图为心理学、管理学、生物学等不具备‘简单可重复性’的学科量身定造出一套检验标准。现在,软科学的概念愈来愈被科学哲学家所重视,它也许会为心理学找到属于自己的科学标准提供一线曙光。
【时代背景·个人机缘】
探讨一个思潮兴衰的时候,中国人历来喜欢从大的角度,如时代背景,来寻找它的兴衰的必然性。但对于大师,对于那些执着于个人探索的研究者而言,时代背景远不如他的个人机缘更为重要。
所谓个人机缘,即,在一个个人的成长之路上,有哪些人成就了他自己。
在探讨罗杰斯的个人机缘的时候,有三个人不可不提:奥托·兰克、马丁·布伯、克尔凯廓尔。
奥托·兰克本来是Freud的门徒,因为提出“与生具来的焦虑和恐惧”,对老师的俄狄普斯情结提出根本性质疑,最终被驱逐。他对强调首先须治疗者领悟,然后将该领悟传授于患者,再由患者领悟的经典精神分析甚未不满。他以为,患者自身具备个人能力,治疗者只是一个积极的协助者,营造出一种情境,使得患者唤起他的积极意志,由此成长。他甚至把自己的他的疗法称作“关系疗法”。1936年期间,罗杰斯邀请兰克到罗切斯特做过三天的演讲。从兰克的疗法中可以看到患者中心疗法的雏形。在讲到影响自己的重要人物时,罗杰斯也从来不忘记感谢兰克。
马丁·布伯的经典著作《我与你》(I and Thou)对关系有精彩绝伦的阐释。他将关系分为两种:我与你、我与它。当把关系的另一方当作可利用的一个目标时,即为“我与它”的关系——勿论该目标何等无私、伟大;当参与关系时,对关系的另一方没有任何预期、任何目的,即可能为“我与你”的关系。只有在“我与你”的关系中,两个人的真本自我才可能映现,并相碰触。
1957年4月,一位马丁·布伯的研究者为罗杰斯、马丁·布伯安排一次会晤。在这之前,罗杰斯的学生已经介绍他阅读了马丁·布伯的著作。会晤中,罗杰斯问马丁·布伯,他的来访者中心疗法的关系是否为“我与你”的关系。马丁·布伯回答说,不是,因为罗杰斯的治疗关系缺乏相互性(reciprocity),治疗者可能会meeting来访者的真本自我,但来访者却不能meeting治疗者。这次会面对罗杰斯有直接影响,在后来的治疗中,他开始注重自己的参与,譬如,自我开放和自我揭露。
但,也许马丁·布伯忘记了一点:meeting只是瞬间,而“我与它”几乎无时不在。治疗者在来访者尚远未“to be that self which one truly is”时,meeting不可能发生。假如治疗者在任一个治疗关系中都将自己的真本自我参与,而很少有来访者的真本自我的回应,枯竭(burn-out)太容易发生。给心理治疗先假定一个“帮助来访者”的唯一目标,并不妨碍罗杰斯的治疗关系的‘我与你’的本质。
比较马丁·布伯的《我与你》同罗杰斯的《A way of being》,会发现,马丁·布伯更形象地抽象,而罗杰斯则非常具体。看了《我与你》,会懂得单纯关系的实质,但只有看了罗杰斯的著作,你才知道该如何做。具体地说,即:在来访者离自己的真本自我很遥远的时候,治疗者的目标就是提供一个安全的关系,唤起他的真本自我,等来访者真正“to be that self which one truly is”的时候,罗杰斯与来访者的两个人的真本自我才可能相遇。而如何建立一个安全的关系呢?罗杰斯最终归纳了三个条件:无条件积极关注、共情、真诚。
马丁·布伯对罗杰斯的另一个明显的影响是,他开始运用马丁·布伯的一些术语来表述他的理论。掌握马丁·布伯的‘我与你’的概念可以很方便地了解罗杰斯。
克尔凯廓尔似乎没有特别体系化的理论,他写的几十部著作只有一个主题:描述他自己的体验世界和他所知觉到的别人的体验世界。读他的著作,会感觉其中的主人公的体验世界和你几乎没有任何距离。同时,其中的体验虽然无比细致、精微,但坦然到你感觉不到丝毫的造作。
克氏是19世纪的人,罗杰斯没有同他相‘meeting’的机缘,但前面曾讲过,感受到如此精妙的体验世界的魅力,直接给了罗杰斯信任、接纳自己的体验的勇气。

【来访者中心·关系】
罗杰斯把自己的疗法称作‘来访者中心疗法’(Client—centered Therapy)。
如果讲有破有立的话,“来访者中心”这个词更像“破”。它“破”的即指导性治疗中,治疗者先掌握一套什么东西,然后将该东西传授给来访者,只要来访者接受、“领悟”到了该东西的内涵,疗效即可发生。与此相反,罗杰斯同兰克一样,他由衷地相信每个个体自身就具备个人成长能力。
那么,什么是罗杰斯的“立”?即关系。兰克已把自己的疗法叫做“关系疗法”,但在罗杰斯那里,他给予了治疗关系以系统、细致的诠释。兰克试图在他的关系里唤起来访者的“创造意志”,而罗杰斯所创立的治疗关系只有一个直接目的:让来访者感到安全。
现在,在任何一个治疗流派中,都一概接受了罗杰斯的治疗关系的几个核心概念,但认为这只是治疗初期、须建立治疗关系时的事情。而对罗杰斯自己来讲,治疗关系就是全部。当一个关系愈能使得一个人安全、自然、无任何防御地展示自己,愈能接受自己的种种体验时,治疗就愈成功。如果说治疗关系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来访者将愈来愈“to be that self which one truly is”。
为什么一个安全的关系会如此重要?因为在日常的关系互动中,每个人的真本自我都已经隐藏,并逐渐被扭曲。
一个个人的成长历程中,获得的积极关注绝大多数为条件积极关注。条件积极关注的逻辑:你必须A,我才能给你B。B可为物质奖赏,也可为主观赞赏。在条件性积极关注的逻辑下,个体会形成这样的经验:只能表露“好”的(或可被接受的),否则,你就会被拒绝、排斥,乃至被伤害。一个个体的成长也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地学习、修正自己“须如何部分地表露”的历程。
这时,一个行为主义的逻辑就会映现:如果条件性积极关注引出了“好”行为,岂不是一件美事!但问题在于,人太丰富,对一个特殊的个体,外在无法界定他的“好”。
存在哲学说:一个人不能替另一个人做选择。罗杰斯则将选择放在了专属于每一个个体的“机体评价过程”上。——仅仅说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还不够,你只有听凭你的“心”,而不是“脑”去选择,你才可能自由。
所谓“机体评价过程”,罗杰斯说,即:须评断、选择时,听从你的机体,远胜于听从你的智力。许多人不理解罗杰斯的“机体评价过程”,认为太抽象、不具体。理解该概念只需要一个前提,即你已经相当地“to be that self which one truly is”了,那个时候,你只须听从你的内心、听从你的第一感觉做选择,就可以了。
但对于习惯了条件性积极关注的个体而言,“机体评价过程”怎么可能?要一个从来都在遵从外在的A的人,忽然就来听从他的“机体”,绝不可能。即便一个个体明白了存在哲学的“自由选择”的含义的人,他仍然不自由,甚至根本不选择,因为他学习、修正得已经迷失了自己的真本自我。罗杰斯的关系治疗,即试图提供无条件积极关注,让来访者感受到,关系还可以这个样子。当来访者切身地感受到这一点后,他起码在这个关系里感到安全,从而放下了防御,开始坦然、真诚地重新体验自己的重要体验,并慢慢地会接受专属于他自己的体验——而这些体验,即他的“我”。当他体验、接受“我”后,他慢慢会获得一种勇气,从而在现实中也能依照“我”的机体评价过程做选择。
对于一个完全“to be that self which one truly is”的治疗者,仅仅无条件积极关注就足够了。可对任一个现实的治疗者,还须做另一个工作:共情(empathy)。
将empathy译成“共情”,有点“神化”它的意思,并经常会令初学者感到,empathy太不可能。Empathy的经典解释是:“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角度,为对方着想的能力”。但确切地说,empathy仅仅是一个技术,它要求治疗者不断地向来访者澄清,“我”有否理解了“你”的体验。有学者说,一个好的治疗者好比一面镜子。Empathy的技术就可以防止治疗者成为一个扭曲的镜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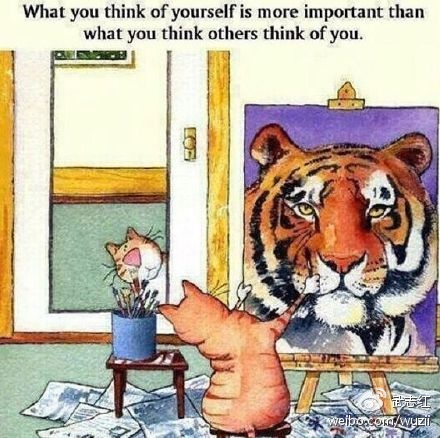
建立一个良好的治疗关系的第三个条件:真诚。
真诚可以看成一个条件,更可以看成一种境界。设想一个做作了四十年的人,忽然要他真诚,他要么根本真诚不了,要么会“真诚”得非常自私、“真诚”得异常自我中心。严格地说,只有对已经“to be that self which one truly is”的人,才可能真诚。
经典的精神分析治疗者在正式做治疗前,首先要有相当长的一段日子被分析。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治疗者在正式做治疗前,也应该首先磨炼自己的真诚。一、学会坦然、真诚地对待自己的体验,并接受;二、学会在关系中毫不犹豫地、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感觉(不是毫不犹豫地表达自己的评价和判断)。一定的程度上,一是二的前提条件,但二亦可帮助一个治疗者达到一。
一定程度上,“关系疗法”也许比“来访者中心疗法”更能概括罗杰斯的理论的精髓。
一些学者质疑:“来访者中心疗法”,会不会使得来访者愈来愈“自我中心”,只顾及自己的需求,完全漠视社会责任。所以如此,完全是因为这些学者没有领会到罗杰斯的治疗关系的内涵。因为罗杰斯在帮助来访者重新体验自己的同时,也帮助来访者学习了一种新的关系——“我与你”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已无所谓“责任”,但对关系、对社会又根本有益。
无妨说,罗杰斯最“to be that self which one truly is”,但能否说罗杰斯漠视社会责任。也许罗杰斯漠视,那只是因为他完全率性而为,而又对社会绝对有益。
【人性善】
来访者中心疗法中,无条件积极关注有一个先定的前提,即:人性善。
无妨逆向地设想:假如人性恶(或者带有恶),“我”如何能给予另一个人无条件的积极关注?
罗杰斯曾与另一个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有过一次论辩。罗洛·梅质疑罗杰斯的人性善,认为人性亦有恶。从两个人交锋的过程上看,罗杰斯似乎占了下风。
但即便人性恶,罗杰斯的“to be that self which truly is”和三个治疗条件的价值并不必然意味着崩溃。
一部著名的小说《发条橙》,讲一个恶少,杀人抢劫,无恶不作,并且,很自然。政府将他抓去,但并没有关在监狱里,而是让一个行为学家来矫正他的行为。矫正很成功,少年出狱后,成了一个“好”公民,听从政府的安排,结婚生子,“正常”地工作,但那都不是他自己的选择——“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完全没有个人意志的参与。
看这部小说后,有一个感慨:即便没有“人”这个东西存在,也胜于一堆完全没有个人意志的“好”人。
在集体主义的社会里,一贯从社会的角度思考价值体系。如此,必然提倡对“恶”的绝对控制和制约。
有两个问题:
一、能否控制得了?
二、从个人的角度上看,假如心中有魔鬼在,如何对待这个魔鬼?
一个设想,对恶的控制和制约并不能起到明显的结果,过度的控制和制约反而会扭曲直接、简单的“恶”。并且,真正破坏社会的、对人类造成巨大伤害的,并不是直接的恶,而是那些扭曲的恶。譬如,无妨夸张些地说,拿破仑的征服欲望是一个直接的恶,它对整个欧洲大陆造成了很大破坏,但同希特勒的“灭绝”的扭曲的恶所造成的伤害相比,简直不能相提并论。再譬如,三国时代,直接的恶充溢着九州,但那却是一段精彩的历史;相对比扭曲的善的南宋,更令人怀念。
由此想,即便人性恶,或有恶,一样也须“to be that self which one truly is”,而一个被扭曲的个体要达到这一点,罗杰斯的三个治疗条件依然具有巨大价值。
善恶也许仅针对关系而言。
人在孤独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being,有了一个选择的自由;人在关系中,又有一个being,有一个选择的自由。人在孤独中,无所谓“善”与“恶”;但在关系中,当关系为“我与你”时,会选择善,当关系为“我与它”时,会选择恶。
作者:武志红
微信:wzhxlx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